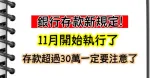3/4
下一頁
丈夫是混蛋,她獨自培養出4位中央委員,臨終不知兒子已壯烈犧牲

3/4
「不會,就學。」她這樣說,也這樣做。
她向鄰居請教最簡單的法語單詞,一邊學一邊寫,半個月後,她已能用蹩腳的發音問價、買菜,三個月後,她竟能看懂簡易的報紙,偶爾還能給孩子們翻譯一兩句。
除了學習,她還用從湖南帶來的絲線和繡花布匹,在法國人眼中如魔術般地做出精緻的湘繡。
她把這些刺繡拿到集市販賣,所得的錢一半用來補貼生活,一半用來資助孩子們謄抄、翻譯馬克思主義書籍。
她從不以為這是「女紅」,她說:「你們用筆寫革命,我用針縫革命。」
有時夜深人靜,她依舊坐在炕邊,聽著蔡和森和向警予討論「無產階級專政」和「階級鬥爭」,嘴角會輕輕翹起。
她不完全懂那些複雜的政治術語,但她知道,這群年輕人肩上,擔著的是未來的中國。
她從不干涉孩子的選擇,更從不以「母親」的身份去擺出架子。
她只是轉身去廚房端出一鍋煮熱的雜糧粥,輕聲說:
「來,吃了這碗粥,好接著想革命的事。」
後來,「中共」的字眼第一次在蔡和森的信中出現,那一刻,她不再只是蔡和森的母親、蔡暢的母親,她成了那個時代最堅韌的革命母親。
她向鄰居請教最簡單的法語單詞,一邊學一邊寫,半個月後,她已能用蹩腳的發音問價、買菜,三個月後,她竟能看懂簡易的報紙,偶爾還能給孩子們翻譯一兩句。
除了學習,她還用從湖南帶來的絲線和繡花布匹,在法國人眼中如魔術般地做出精緻的湘繡。
她把這些刺繡拿到集市販賣,所得的錢一半用來補貼生活,一半用來資助孩子們謄抄、翻譯馬克思主義書籍。
她從不以為這是「女紅」,她說:「你們用筆寫革命,我用針縫革命。」
有時夜深人靜,她依舊坐在炕邊,聽著蔡和森和向警予討論「無產階級專政」和「階級鬥爭」,嘴角會輕輕翹起。
她不完全懂那些複雜的政治術語,但她知道,這群年輕人肩上,擔著的是未來的中國。
她從不干涉孩子的選擇,更從不以「母親」的身份去擺出架子。
她只是轉身去廚房端出一鍋煮熱的雜糧粥,輕聲說:
「來,吃了這碗粥,好接著想革命的事。」
後來,「中共」的字眼第一次在蔡和森的信中出現,那一刻,她不再只是蔡和森的母親、蔡暢的母親,她成了那個時代最堅韌的革命母親。
 呂純弘 • 11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1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1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10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1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