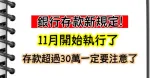2/4
下一頁
丈夫是混蛋,她獨自培養出4位中央委員,臨終不知兒子已壯烈犧牲

2/4
她心裡苦笑,自己連「齊家」都無從談起,還如何指望教出有志氣的兒女?
終於,在某個清晨,她推開蔡家的門,帶著孩子離開了上海,回到了荷葉鎮老家。
老家的日子並不比上海輕鬆,蔡蓉峰依舊不知悔改,一副「家中主子」的模樣,對她指手畫腳,吆五喝六。
他開始逼她給年幼的女兒裹腳,說「不裹小腳,將來沒人要」,還要兒子去田間做工,說「讀書是浪費銀子」。
她聽了這話,咬牙不語,回房後,她將自己的嫁妝細細清點,把壓箱底的金銀首飾和繡花被面拿出來,一件件賣掉,為的只是能湊足蔡和森的學費。
有一次,蔡蓉峰酒後發瘋,要強行給小女兒裹腳,葛蘭英抱著女兒逃進鄰居家,把自己反鎖在柴房裡整整三天,守著女兒不讓他碰。
日子一天天地熬,直到她遇到了兩個女人,秋瑾與唐群英。
她與她們交往越深,越感羞愧,她說自己「生得是女人的身子,卻被囚於男人的世界太久」。
在秋瑾遇害後,葛蘭英在家中設了靈堂。
她告訴自己:「我不能像她們那樣投筆從戎,但我可以教我的兒女做他們做的事。」
她第一次向父母提出休夫請求。
父母勸她「女人家就該認命」,她冷笑一聲,道:
「認命?我早該死在書堆里,不該嫁進這狗窩裡!」
休夫一事,在鄉里引起轟動,女人休夫,這在那個年代簡直比「忤逆父母」還重。
但她並不在意。
她要的是孩子讀書,是女兒不纏足,是孩子們有一個不被父權壓迫的未來。
她親手為小女兒解開腳布,為兒子挑選筆墨紙硯,為大女兒打制布鞋出門看學塾。
她終於開始活成了自己。
半百求學
1914年的長沙,大多數人家的女人們都守著火爐做針線,或趕在年關前去廟裡添香祈福。
但就在這被寒意和傳統緊緊包裹的省城,一位身著舊棉袍、腳踩厚布鞋的中年婦人,帶著兩個女孩,站在了湖南女子教員養成所的大門前。
那人不是別人,正是年近五十的葛蘭英。
養成所的大門高高的,牌匾上的四個燙金大字在冬日陽光下微微泛著光。
葛蘭英昂首走進去,身後跟著的大女兒蔡慶熙、小女兒蔡暢,還有年僅五歲的外孫女劉昂。
她早已打聽清楚,這是一所專為培養女性教師開設的新式學校,凡女子若有高小文化基礎,皆可報考。
她自小通讀《四書》《五經》,識文斷字不在話下,自信滿滿。
可她剛進門,就被門口登記的女教務攔了下來。
「這位夫人,您是來為哪位小姑娘報名的?」女教務員見她頭髮花白,語氣格外溫和。
葛蘭英回以淡然一笑:「我是來給我自己報名的。」
話音一落,女教務員頓時怔住,隨後為難地道:
「學校有規定,學員需為適齡女子……」
「適齡?」葛蘭英直視她,「請問是幾歲到幾歲?」
那人張口結舌:「這……沒有明確,但從未有過您這樣的年紀。」
葛蘭英不爭不吵,拉過蔡和森寫好的一封狀紙,道:
「若你們不收,我自會向長沙縣衙遞狀。」
隨後,她轉身,帶著女兒和外孫女轉頭離去,數日後,長沙縣知縣在大堂上展開那封狀紙。
他一字一句地讀完狀紙後,隨手提筆,在末尾批了四個大字:「奇志可嘉」。
這四個字,在當時的長沙掀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。
一紙狀書破了舊規,那位「年紀最大的新生」,理直氣壯地進入了養成所課堂,坐在比她小了三十歲的姑娘中間聽課、寫字、做體操。
她不羞、不怯、不退,自覺自己不是與人攀比的「老太婆」,而是一位肩負使命的「新女學士」。
她每天清晨最早到教室,夜裡燈滅後仍借油燈苦讀,尤其偏好唐詩與經義,有時甚至背誦得比老師還熟。
幾個月後,那些曾對她指指點點的年輕學員,竟紛紛圍在她身邊,請教國文、詩詞、甚至女紅。
她逐一耐心解答,毫無架子。
漸漸的,她從「那個老太婆」變成了「葛大姐」「葛伯母」。
同學中稱她「學問有餘,精神更盛」,老師們也常以她為榜樣。
與此同時,葛蘭英將自己的名字,鄭重地改為「葛健豪」。
健者,改造舊社會之健將,豪者,打倒舊枷鎖之豪傑。
舊的葛蘭英,已經死了,她要做的,是新中國的新母親、新女子。
她用行動告訴世人,讀書與改變命運,從來不設門檻,唯有不甘與不屈,是所有女性最強大的入場券。
育子赴法
長沙劉家台子的那間小屋,並不寬敞,屋內擺著一張老舊木桌、一架縫紉機、一方灶台。
若不是那張桌前,經常圍坐著一群眼神熾熱、談笑風生的年輕人,誰也不會想到,這樣一個尋常的農家屋角,竟是那個時代最早的革命火種發源地之一。
那群年輕人,有毛澤東、蔡和森、向警予、羅章龍、何叔衡……
他們以葛健豪家為據點,探討理想、策划行動、閱讀譯文,推演未來的中國。
每次開會前,他們都先圍到後院幫著幹活,翻菜地、挑水、拾柴火。
開完會後,幾人擠在灶前吃飯,一碗稀飯、一碟豆腐乳,香得能吃下三碗乾飯。
而這一切的中心人物,是那位腳穿布鞋、身著粗布衣的老母親,葛健豪。
這看似平常的日子,其實藏著無數不平常的細節。
一到夜裡,燈芯挑高,葛健豪就在縫紉機前忙個不停。
不是給孩子們縫補衣服,就是在為即將遠行的兒女縫製行囊。
蔡和森和蔡暢準備出國留學的那段時間,是她最忙碌也最沉默的時光。
她知道孩子們去法國,不是為了鍍金,而是為了更廣闊的革命理想。
而她能做的,就是讓他們衣著得體、不至寒冷,行李整齊、少一分麻煩。
臨行前,旅費仍是難題,她沒有猶豫,取出所剩不多的嫁妝,拿到當鋪一一折現。她還找到曾國藩的外孫、愛國實業家聶雲台,開口借了六百銀元。
那年,她五十四歲,帶著女兒、女婿、外孫,加入了三十人的留法勤工儉學隊伍,踏上了駛往法國的郵輪。
初來乍到的中國青年們因語言不通、生活艱難,常被法國人冷眼相待。
葛健豪一開始連刀叉都拿不穩,法語更是一個字也不懂,但她沒有退縮。
終於,在某個清晨,她推開蔡家的門,帶著孩子離開了上海,回到了荷葉鎮老家。
老家的日子並不比上海輕鬆,蔡蓉峰依舊不知悔改,一副「家中主子」的模樣,對她指手畫腳,吆五喝六。
他開始逼她給年幼的女兒裹腳,說「不裹小腳,將來沒人要」,還要兒子去田間做工,說「讀書是浪費銀子」。
她聽了這話,咬牙不語,回房後,她將自己的嫁妝細細清點,把壓箱底的金銀首飾和繡花被面拿出來,一件件賣掉,為的只是能湊足蔡和森的學費。
有一次,蔡蓉峰酒後發瘋,要強行給小女兒裹腳,葛蘭英抱著女兒逃進鄰居家,把自己反鎖在柴房裡整整三天,守著女兒不讓他碰。
日子一天天地熬,直到她遇到了兩個女人,秋瑾與唐群英。
她與她們交往越深,越感羞愧,她說自己「生得是女人的身子,卻被囚於男人的世界太久」。
在秋瑾遇害後,葛蘭英在家中設了靈堂。
她告訴自己:「我不能像她們那樣投筆從戎,但我可以教我的兒女做他們做的事。」
她第一次向父母提出休夫請求。
父母勸她「女人家就該認命」,她冷笑一聲,道:
「認命?我早該死在書堆里,不該嫁進這狗窩裡!」
休夫一事,在鄉里引起轟動,女人休夫,這在那個年代簡直比「忤逆父母」還重。
但她並不在意。
她要的是孩子讀書,是女兒不纏足,是孩子們有一個不被父權壓迫的未來。
她親手為小女兒解開腳布,為兒子挑選筆墨紙硯,為大女兒打制布鞋出門看學塾。
她終於開始活成了自己。
半百求學
1914年的長沙,大多數人家的女人們都守著火爐做針線,或趕在年關前去廟裡添香祈福。
但就在這被寒意和傳統緊緊包裹的省城,一位身著舊棉袍、腳踩厚布鞋的中年婦人,帶著兩個女孩,站在了湖南女子教員養成所的大門前。
那人不是別人,正是年近五十的葛蘭英。
養成所的大門高高的,牌匾上的四個燙金大字在冬日陽光下微微泛著光。
葛蘭英昂首走進去,身後跟著的大女兒蔡慶熙、小女兒蔡暢,還有年僅五歲的外孫女劉昂。
她早已打聽清楚,這是一所專為培養女性教師開設的新式學校,凡女子若有高小文化基礎,皆可報考。
她自小通讀《四書》《五經》,識文斷字不在話下,自信滿滿。
可她剛進門,就被門口登記的女教務攔了下來。
「這位夫人,您是來為哪位小姑娘報名的?」女教務員見她頭髮花白,語氣格外溫和。
葛蘭英回以淡然一笑:「我是來給我自己報名的。」
話音一落,女教務員頓時怔住,隨後為難地道:
「學校有規定,學員需為適齡女子……」
「適齡?」葛蘭英直視她,「請問是幾歲到幾歲?」
那人張口結舌:「這……沒有明確,但從未有過您這樣的年紀。」
葛蘭英不爭不吵,拉過蔡和森寫好的一封狀紙,道:
「若你們不收,我自會向長沙縣衙遞狀。」
隨後,她轉身,帶著女兒和外孫女轉頭離去,數日後,長沙縣知縣在大堂上展開那封狀紙。
他一字一句地讀完狀紙後,隨手提筆,在末尾批了四個大字:「奇志可嘉」。
這四個字,在當時的長沙掀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。
一紙狀書破了舊規,那位「年紀最大的新生」,理直氣壯地進入了養成所課堂,坐在比她小了三十歲的姑娘中間聽課、寫字、做體操。
她不羞、不怯、不退,自覺自己不是與人攀比的「老太婆」,而是一位肩負使命的「新女學士」。
她每天清晨最早到教室,夜裡燈滅後仍借油燈苦讀,尤其偏好唐詩與經義,有時甚至背誦得比老師還熟。
幾個月後,那些曾對她指指點點的年輕學員,竟紛紛圍在她身邊,請教國文、詩詞、甚至女紅。
她逐一耐心解答,毫無架子。
漸漸的,她從「那個老太婆」變成了「葛大姐」「葛伯母」。
同學中稱她「學問有餘,精神更盛」,老師們也常以她為榜樣。
與此同時,葛蘭英將自己的名字,鄭重地改為「葛健豪」。
健者,改造舊社會之健將,豪者,打倒舊枷鎖之豪傑。
舊的葛蘭英,已經死了,她要做的,是新中國的新母親、新女子。
她用行動告訴世人,讀書與改變命運,從來不設門檻,唯有不甘與不屈,是所有女性最強大的入場券。
育子赴法
長沙劉家台子的那間小屋,並不寬敞,屋內擺著一張老舊木桌、一架縫紉機、一方灶台。
若不是那張桌前,經常圍坐著一群眼神熾熱、談笑風生的年輕人,誰也不會想到,這樣一個尋常的農家屋角,竟是那個時代最早的革命火種發源地之一。
那群年輕人,有毛澤東、蔡和森、向警予、羅章龍、何叔衡……
他們以葛健豪家為據點,探討理想、策划行動、閱讀譯文,推演未來的中國。
每次開會前,他們都先圍到後院幫著幹活,翻菜地、挑水、拾柴火。
開完會後,幾人擠在灶前吃飯,一碗稀飯、一碟豆腐乳,香得能吃下三碗乾飯。
而這一切的中心人物,是那位腳穿布鞋、身著粗布衣的老母親,葛健豪。
這看似平常的日子,其實藏著無數不平常的細節。
一到夜裡,燈芯挑高,葛健豪就在縫紉機前忙個不停。
不是給孩子們縫補衣服,就是在為即將遠行的兒女縫製行囊。
蔡和森和蔡暢準備出國留學的那段時間,是她最忙碌也最沉默的時光。
她知道孩子們去法國,不是為了鍍金,而是為了更廣闊的革命理想。
而她能做的,就是讓他們衣著得體、不至寒冷,行李整齊、少一分麻煩。
臨行前,旅費仍是難題,她沒有猶豫,取出所剩不多的嫁妝,拿到當鋪一一折現。她還找到曾國藩的外孫、愛國實業家聶雲台,開口借了六百銀元。
那年,她五十四歲,帶著女兒、女婿、外孫,加入了三十人的留法勤工儉學隊伍,踏上了駛往法國的郵輪。
初來乍到的中國青年們因語言不通、生活艱難,常被法國人冷眼相待。
葛健豪一開始連刀叉都拿不穩,法語更是一個字也不懂,但她沒有退縮。
 呂純弘 • 11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1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1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10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1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