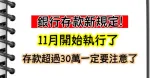6/7
下一頁
他是翻譯整個中國的泰斗,活到95歲,兒子36歲自焚去世

6/7
天放晴了,別人放過他了,可他心裡的魔鬼還揪著他不放。
戴乃迭將兒子送去英國妹妹家,讓他換個環境換個心情,殊不知送兒子上郵輪時,已經是他們此生的最後一面。
在英國的每一天,那個魔鬼無時無刻不在挑釁他,拖著他,拽著他,踩著他。
他的身體越發膨脹,這個世界逐漸腐爛,兩個正在朝死亡發展的屍首背對背拴在一起,相互墜著,往下沉。
他放火燒了36歲的自己。戴乃迭大病一場,兒子成了家裡的禁忌,誰都不敢提起,朋友去探望兩位,也是自覺跳過這個話題。
傷口並沒有癒合,只是被晾在一邊,誰都不敢去碰它,仿佛不碰它,就不痛,不痛就沒發生過。
兩人只是越來越喜歡喝酒,喝個爛醉,再搖搖晃晃上床睡覺。
醉酒時被床下的拖鞋絆倒,還能若無其事上床睡覺,清醒時滿地的往事,看得再清,他們也很難擔保自己不會被絆倒,順利跨過去,安然上床入睡。
後來,酒也沒用了,戴乃迭患上了老年痴呆,老伴得了痴呆,楊憲益也必須清醒,他謝絕了一切聚會,一心在家照顧戴乃迭。
朋友李輝曾上門一次,那時戴乃迭坐在輪椅上,已完全痴呆,楊憲益跟他聊天,時不時給她擦擦嘴角,喂她喝口水。
1999年,還有一個半月就要走向下個世紀,戴乃迭走了,她愛楊憲益,可她也深愛那個可憐的孩子,她不忍心把他獨自撇在舊的世紀。
愛人的骨灰,楊憲益沒有留,他捨不得她,可他也想讓他們娘倆團聚。
最後,他賦詩淚別愛人:
早期比翼赴幽冥,不料中途失健翎。
結髮糟糠貧賤慣,陷身囹圄死生輕。
青春作伴多成鬼,白首同歸我負卿。
天若有情天亦老,從來銀漢隔雙星。
戴乃迭走後,楊憲益的翻譯生涯也終結在了這一年,他沒再翻譯其他作品,做回了「酒鬼」。
喝一口,講兩句,喝到最後,話囫圇吐在了酒里,沒話可說了,就悶頭喝,把心事喝了回去。
一天喝掉半瓶威士忌,都是常有的事。
他也不忌諱死亡,朋友聚會他常開玩笑道,「我的追悼會得趕快開,人說好話的時候都是在追悼會上說,人已經死了才去說,有什麼用,所以我們早點開。」
後來,他喉嚨長了瘤子,他拒絕了治療,說無所謂了。
妹妹楊苡腿部骨折,一直惦記著要到北京來給哥哥過94歲生日。
好在2008年,心愿得償,兄妹三人又聚到了一起,這也是楊憲益的最後一個生日。
戴乃迭將兒子送去英國妹妹家,讓他換個環境換個心情,殊不知送兒子上郵輪時,已經是他們此生的最後一面。
在英國的每一天,那個魔鬼無時無刻不在挑釁他,拖著他,拽著他,踩著他。
他的身體越發膨脹,這個世界逐漸腐爛,兩個正在朝死亡發展的屍首背對背拴在一起,相互墜著,往下沉。
他放火燒了36歲的自己。戴乃迭大病一場,兒子成了家裡的禁忌,誰都不敢提起,朋友去探望兩位,也是自覺跳過這個話題。
傷口並沒有癒合,只是被晾在一邊,誰都不敢去碰它,仿佛不碰它,就不痛,不痛就沒發生過。
兩人只是越來越喜歡喝酒,喝個爛醉,再搖搖晃晃上床睡覺。
醉酒時被床下的拖鞋絆倒,還能若無其事上床睡覺,清醒時滿地的往事,看得再清,他們也很難擔保自己不會被絆倒,順利跨過去,安然上床入睡。
後來,酒也沒用了,戴乃迭患上了老年痴呆,老伴得了痴呆,楊憲益也必須清醒,他謝絕了一切聚會,一心在家照顧戴乃迭。
朋友李輝曾上門一次,那時戴乃迭坐在輪椅上,已完全痴呆,楊憲益跟他聊天,時不時給她擦擦嘴角,喂她喝口水。
1999年,還有一個半月就要走向下個世紀,戴乃迭走了,她愛楊憲益,可她也深愛那個可憐的孩子,她不忍心把他獨自撇在舊的世紀。
愛人的骨灰,楊憲益沒有留,他捨不得她,可他也想讓他們娘倆團聚。
最後,他賦詩淚別愛人:
早期比翼赴幽冥,不料中途失健翎。
結髮糟糠貧賤慣,陷身囹圄死生輕。
青春作伴多成鬼,白首同歸我負卿。
天若有情天亦老,從來銀漢隔雙星。
戴乃迭走後,楊憲益的翻譯生涯也終結在了這一年,他沒再翻譯其他作品,做回了「酒鬼」。
喝一口,講兩句,喝到最後,話囫圇吐在了酒里,沒話可說了,就悶頭喝,把心事喝了回去。
一天喝掉半瓶威士忌,都是常有的事。
他也不忌諱死亡,朋友聚會他常開玩笑道,「我的追悼會得趕快開,人說好話的時候都是在追悼會上說,人已經死了才去說,有什麼用,所以我們早點開。」
後來,他喉嚨長了瘤子,他拒絕了治療,說無所謂了。
妹妹楊苡腿部骨折,一直惦記著要到北京來給哥哥過94歲生日。
好在2008年,心愿得償,兄妹三人又聚到了一起,這也是楊憲益的最後一個生日。
 呂純弘 • 11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1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1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10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1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